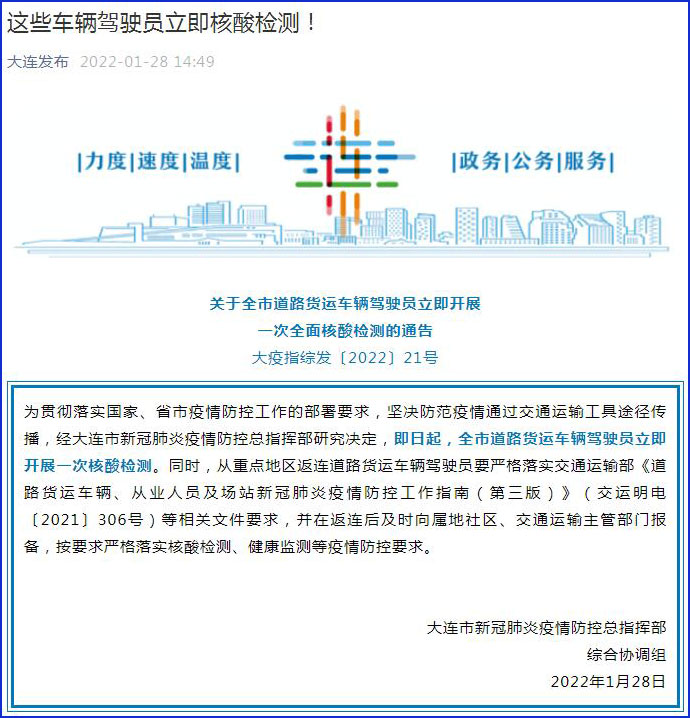假的女莎士比亚,真的女性主义|伍尔夫诞辰140周年
一只疾飞的昆虫在黄昏时分出现。它是灰色的,毛茸茸的翅膀,绕着报春花的黄花盘旋。一群年轻人,手里提着毒药罐,手持捕蝶网,嘁嘁喳喳地走进树林,靴子在硬质的路上擦得嘎嘎响。捕蝶网不捕蝴蝶,而是冲着那只灰色的大飞蛾去的。这条路通往一片黑暗的未知世界——树林,乔木和灌木,在灯笼火光的照耀下,披上了淡绿色的夜礼服。
队长领着头:“看!”他指向草丛,提灯周围有许多昆虫在飞舞;年轻人用一块法兰绒——蘸了糖浆、甜酒,吸引来了众多飞蛾,它们贪婪地吸吮着那甜蜜的糖汁,灯光已经将它们彻底罩在了里面,也依然不肯离去,只有翅膀在抖动,似乎有些不安。
但他们还在等待那只最大的飞蛾。尤其是队伍里的一个女孩子,她紧张地瞅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她有一双显微镜一般的眼睛,能看到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物。这时,大飞蛾出现了,就像凤凰一样,立刻让百鸟暗淡下去;它的内翼是猩红色的,威风八面,似乎傲视一切的样子,但它一降落,就好像意识到这是个陷阱,于是又扑扑翅膀,漫不经心地飞走了。
人们用灯光追逐它,它不见了,人们放弃了。但当他们一行人离开这里,走向树丛边缘时,他们蓦然看到,那只大飞蛾就停在一棵最遥远的树的树干上。它也许只是一瞬间麻痹大意了。它立刻被抓住,毒药罐子把它扣在里面,当它临死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听到了一阵响声,那是黑暗中,一棵大树倒下了。
飞蛾,俊美而脆弱,潜行于夜间,像晚会上的巨星一样压轴登场,飘然而过却又在劫难逃。那女子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若干年之后,她用文字将这只飞蛾重现了出来:它死去了,这个追求甜蜜、光明的骄傲的牺牲者,无法解释它死时大树的砰然倒地,唯一能够说明的,是伍尔夫曾经许多次地与飞蛾相遇,熟悉它们不顾一切和被捕获时安然的样子,也熟悉在黑暗中看东西的样子。她知道,自己看到的不是客观现实,而是自己的意识认为自己看到的东西。
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驱者之一。代表作有《夜与日》《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遗产》《一间自己的房间》《普通读者》《飞蛾之死及其他》等。
姐妹
飞蛾是弗吉尼亚潜意识里的自我化身。潜意识是一片黑暗之水,人必须趁夜去体验沉入其中的感觉。在幼年,弗吉尼亚以追随飞蛾来体会黑暗的时候,她就将自己投放入一种命运:她也要成为那个被追捕的对象,将被不知名的敌对力量所摧毁。
在家里,她身边就有一只蝴蝶——她姐姐瓦内莎(Vanesa),这个名字,是一种蝴蝶的名字,中文翻译成“苧蝶”。姐妹两个关系一直很好,都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的严肃管教下长大,共同抵触父亲的权威。她们彼此商定,姐姐以画画为业,妹妹则专事文学;但她们两个之间也有竞争,弗吉尼亚看到瓦内莎站在画架前画画,就也找人打造了一张书桌,让她得以在书桌前站着写作。
弗吉尼亚逐渐活成了瓦内莎的一个阴影——相对于日光下翩翩的蝴蝶,夜间出没的飞蛾就是影子一般,又像是一张负片,颜色与自然光下的色彩相反,凭意识的触角觅食,来到森林的深处。这片潜意识的森林储存着那些早已发生过的事情,储存了很久以前听到的响动、看到的图景。
弗吉尼亚的身体也比瓦内莎差很多。困扰她的最大的病灶就是精神分裂。从1895年,她15岁开始,到她42岁写出长篇小说《雅各之屋》,12年间,她曾五次出现精神崩溃的情况。但生病对于一个夜行动物来说似乎是必需的:每次身体疼痛,头脑中就会有什么东西涌出,又好像有一双翅膀在头脑中扑打,她能听见它们的声音。因此,每次开始卧床,她就明白自己又有新的作品可以写出来了,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一只蛹的状态,在蛰伏,在酝酿起飞。
那双翅膀从小小的蛹中挣扎着冒出来,那么大,却又完好无损,这种自然界里难以解释的奇迹,完美地对应于弗吉尼亚和她的小说:一个渺小而虚弱的身体,创出了完整而不失为“宏大”的文字结构。那就是1922年的《雅各之屋》。因为她太虚弱,所以弗吉尼亚的朋友,或者一些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到此为止了,这么一本书——如此细腻和诡异,却又能够成立,可想而知耗费了多少心力——足以把她榨干。小说里连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都没有,很难想象,弗吉尼亚还能继续产出这样的作品。
她的精神状态也令人疑惑、担忧,书出版的前后,她陷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写作显然直接影响到了她的健康和理智。
父亲
可是,过了5年,她在日记里说:别人当初都说我到此为止了,说我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可我看到这条胡同延伸得很长很长,在胡同的远处,站着一个老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老人?他是一个威严的家长,用自己的胡子和胡子上方威严的目光来控制人——控制他的女儿。他就是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或者说,是一个死去的上帝。莱斯利生于1832年,逝世于1904年。1928年12月28日,弗吉尼亚写下了一则日记:
“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如果他不死,他应该是96岁了。是的,今天他本来应该是96岁了。像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人一样,他本来可以活到96岁;但上帝大发慈悲,没有让他活到那么老。他的寿命会把我的生命全都给毁了。如果他长寿,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什么也写不成,书也出不了——真是不可想象。”
正是靠了这种对父亲的执念般的思忖,弗吉尼亚出人意料地“续命”了。她开始写她的《到灯塔去》。
女儿很难推翻父亲,不管他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不管她是敬爱他更多一些,还是畏惧和厌恶他更多一些。如她所讲,父亲的形象在她个人的生活中,以及在她想象的生活中,何其鲜明而强硬,倘若父亲一直活着,那么她的创作只能终止,因为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家长,在把女儿们培养成贤明乖顺的主妇这一点上,莱斯利·斯蒂芬自认责无旁贷,而且志在必得。弗吉尼亚后来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谈到英国出产的最伟大的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她说:莎士比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妹妹,而我是她的后辈。这位女莎士比亚写诗,水平不亚于她那位天才的哥哥,然而社会习俗不允许女性公开创作,也因为她没有经济独立的可能,她的诗被人冷落,她被人羞辱。
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女莎士比亚,弗吉尼亚想象出了这么一个人,以此举例,说明在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女性是一条被压抑的潜流,因为缺乏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女性没有声音。
而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里,她也写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男孩,如何同父亲争夺母亲。有一天,詹姆斯的妈妈跟他保证说,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以到灯塔去。听了这话,詹姆斯就觉得,灯塔这么一个奇观,好像已经很近了,只要经过一个漆黑的夜晚和一个白昼的航行,就能看到它,而航行途中的任何耽搁、考验和折磨,都会把航行变成一次出色的远征,让目的地的景色更加瑰奇壮丽。
但是,在妈妈给出保证之后,父亲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但是天气是不会好的。”
这就是弗吉尼亚眼中的父亲,一个惯于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驳斥孩子的梦想的人。他是一个老人,一个揭露者和反对者,詹姆斯的梦幻被他戳破了,他说,假如自己当时手边有把斧子,或者有把火钳,或者任何可以在父亲的胸口戳个窟窿并且杀掉他的凶器,他都会马上抓到手里……
多年以后,詹姆斯已经许多次去过灯塔了,但是,当他最后一次出航去灯塔时,他仍然以为自己将像以往一样想起父亲,父亲正坐在他的面前,随时可能站起来责骂他,而他,詹姆斯,就准备要抄起一把刀子刺向父亲。但实际上,这一次,他的眼前却出现了一个小孩,正坐在童车里,看见一辆车在不知不觉中压坏了某人的一只脚。这只脚变成了紫色。这番景象,表明詹姆斯知道,在他意识到父亲给他带来的伤害时,这伤害早已产生了,他那个本该幸福的童年世界已经凋零、枯萎了。“但是天气是不会好的。”父亲的这句话压在了他人生中,迫使他睁开眼,去看向大海的前方,看向那座影影绰绰的灯塔:那是他消失已久的母亲,是一个女性长辈,也是弗吉尼亚本人所想象的,那个被压抑住的文学前辈——女性的莎士比亚。
布鲁姆斯伯里
可是《到灯塔去》的主人公詹姆斯毕竟是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弗吉尼亚并没有兴趣去把一个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活灵活现地写出来,将她变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从而为后人所谓的“女性主义”提供什么激励。在她这里,现实世界,远不只是一个女人被男人压迫、必须与男人争斗的世界,相反,她认为只要是有创作才能的人,不论男女,都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对同样的处境——都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
对她来说,这间屋子,可以说就是布鲁姆斯伯里。这是伦敦戈登广场的一所宅第,在那里,从1905年开始,弗吉尼亚姐妹和她们的两个兄弟索比和阿德里安,每个星期都举办友人聚会。从晚上十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两三点,一群人喝着威士忌,吃着小面包,侃侃而谈。没错,这是一些精神贵族,不客气地说,是一些四体不勤的社会寄生虫,他们的生活阅历狭窄,活动范围有限,以文学为高雅的消遣,以精妙地赏析各种作品、摈弃无聊平庸的东西并深耕感受力和幽默为志趣,而不是像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这几位常常被等同于“文学”本身的大作家那样,以改变世道,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为己任。
这个小团体受到无数批评和鄙视,他们以艺术为宗教,相信神秘主义,好像逆历史潮流而动。可是弗吉尼亚和她喜欢的那些兄弟、朋友,却反过来还要社会称赞他们,称赞他们顶级的审美趣味和清高的、蔑视一切的作风。这个小团体,也正是在1904年,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死后才形成的。父亲逝世时,弗吉尼亚没有显得多么伤心,相反,她忙于对前来吊唁的人做各种挑剔:她读那些吊唁信,那些讣告,觉得信中用的词句都十分庸俗,很不准确;有个女人前来看望他们,她说话特别快,弗吉尼亚立刻就听不下去了,她做出了一副十分疲惫的样子,让那个女人早点走人。
权威赫赫的男性家长,在弗吉尼亚的眼前让开了位置——她得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可是这间屋子里,她喜欢的那些人却无法久住。疾病,是那么容易通往绝症,在那些年里,和战争一样,是萦绕在所有人头顶的阴云。就在父亲去世后两年,弗吉尼亚挚爱的哥哥索比,竟然因为伤寒而早逝,年仅26岁。这件事带来的悲伤,和对这种悲伤的反复咀嚼,让弗吉尼亚更加不屑于为自己那种冷视世俗的眼光辩解,她知道,她所拥有的绝不只是世人眼里的安逸生活,她拥有的是一种心理活动,它远远高于生活本身。
飞蛾
她在之后几年里写了一些小说,看得出来,她是在适应哥哥去世的事实。在这些小说里,断断续续地,出现了飞蛾。有时候,飞蛾出现在一个人坠入爱河的时候,有时候,又出现在人死去之后。飞蛾总是神秘的,别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出现,因为它属于夜晚,本该是看不见的;当它越过了白昼和黑夜的界线,出现在人们眼前,或许就带着另一个世界的信息。
弗吉尼亚有一则散文,叫《读书》,既然叫“读书”,那就该好好地写自己的阅读经历,可是,正是在这篇文章进入高潮的地方,她写到了开头所说的,一行人走进森林深处诱捕飞蛾的经验:黑暗中的一盏灯,召唤飞蛾从黑暗中浮现,纷至沓来,在草丛里发光,带着翅膀上的各种磨损,各种在尘世间沾染的污垢,各种透露着遗传基因的色彩和斑点。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对生命中的挚爱献上缅怀的方式,就是把下雨看作天空的泪滴,把变化的光线看作故人目光的闪烁,在树叶和花朵中找到各种思念的载体。但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这还不够。飞蛾,也许起初,一度是她哥哥索比在天之灵的化身,但后来,当活人留给她的印象越来越淡漠,她就把飞蛾看作了她自己感受中的各种词汇,词汇和飞蛾的翅膀一样,围绕着一点光亮,若隐若现,只有随时专注而聪慧的头脑才可以捕获。
当她在1926年9月,写《到灯塔去》的时候,她忽然在一则日记中说:“每个早晨,我在准备写作之前,总是用自己的触角在空中四处探索”——这时,她已经和她四处寻找的词汇合二为一了,也和她的哥哥索比,和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布鲁姆斯伯里时光——不分彼此了。为此,她付出了5次精神崩溃,以及常年病痛缠身的代价,而她也在对阵疾病和崩溃之中,实现这样一种转化。
病痛与意识流
健康对弗吉尼亚的意义,和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同。在疾病面前,所谓的正视和超越疾病,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利用发烧来感受体温的变化,她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生物的自然凋谢、蛰伏,她的精神活动,有时候不得不停顿下来,于是又回归了蛹的状态。她在一篇日记里说,即使是轻微的感冒,打几个喷嚏,也是对人有利的,因为:
“当健康的光焰微弱时,那未曾发现的国度就显露了出来,那灵魂中的荒原和沙漠……那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橡树,被疾病连根拔起,它带来的精神变化何等巨大,何等惊人。在疾病中,人的思想,仿佛经历了一场使沙漠变成沃土、让野蛮人得到教化的世界大战,思想渴望健全,从而让感官恢复平衡。人的理智,应该是失去约束、到处游荡的,这将使我们恢复孩子的眼睛。”
那未发现的国度,那潜意识的国度,不是医生在病历本上潦草的记录,而是一篇篇文章和小说里披露的角落。她的头脑不能懈怠,否则就要从那个空间里滑落出来,被迫与自己破碎的肉身孤独相依了。于是,她总是迫不及待,在一部作品接近完成的时候赶忙构思下一部。《到灯塔去》写完之前,她决定,把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就命名为《飞蛾》。
这本书,将没有连贯的情节,而只有思想意识的流动,它们就像飞蛾,这种最最捉摸不定的昆虫。“印象”这个词,我们都会用,但画家想要逼近它、呈现它,作家想要用文字记录它、描绘它,是需要天才的。欧洲的印象派画家做到了,他们描绘出的图像,完全不同于客观事物却超越于事物之上,而弗吉尼亚说,我要去书写的那种东西,像是一种用神经纤维探触到的褶皱一般的薄膜。意识造就了印象,而文字要书写它,近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后来这本书真的问世了,它不叫《飞蛾》,而叫《海浪》。海浪是一重重涌起又落下的能量,是任性流动、无法用物理工具丈量和推算的东西,它取代了飞蛾,来代表弗吉尼亚心目中,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无穷的创造。
没有几个人能够读进去这本书,因为书中的6个人物,从人生开始产生意识,到一个个离开人世,他们生活的全部经历都深藏在内,他们都属于那座幽暗的森林。但这时,弗吉尼亚已不在乎《海浪》能否赢得几个读者。她是一个点灯的人,吸引着人物像飞蛾一样聚集,可她不会就此转而描绘那些飞蛾的样子:因为她忠实于自己的眼睛,眼睛并没有看清,只是感觉翅膀在亮光周围忽闪;这时,头脑在设法从混沌中提炼形态,不顾一切地将它们形诸文字,有时候,这文字让人豁然开朗,有时候则让人继续困惑,继而沉迷。
她在另一篇散文里,写了她观察到的一只撞击窗玻璃的飞蛾。它横着竖着撞过去,朝着窗外的光亮,一次次地失败,最后落到窗台上。这不是晚上,而是正午,飞蛾不应该出来,但它的细腿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艰苦地搏斗。它终于翻过身来,这是一个赢得了尊严和同情的动作,随即它的身体就僵硬了。微不足道的胜利之后,是永久的安宁。对弗吉尼亚来说,这渺小的飞蛾之死,足以让一个超级的审美头脑进入癫狂,也足以让她身外,那个秩序井然、活在虚荣和确信之中的英国社会悄然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