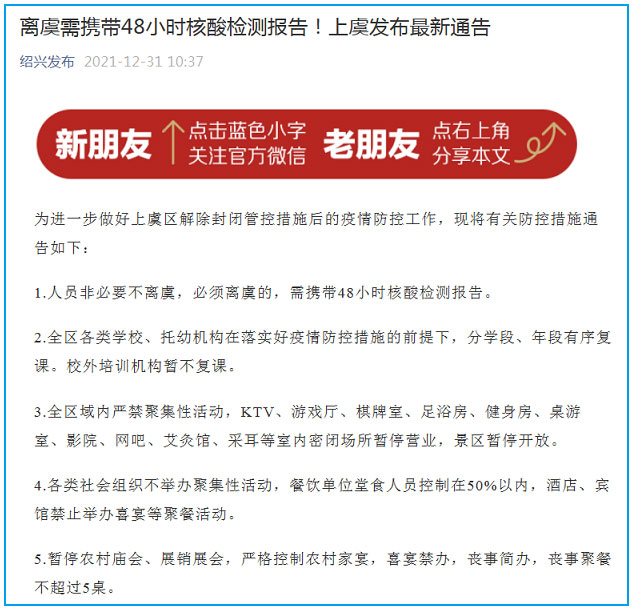不读《包法利夫人》,读读福楼拜150年前的狂野书信
福楼拜在完成了《包法利夫人》第二部分第九章后,发狂一样地写道:“写作是件赏心乐事啊,你不再是你自己啦,你走进了一个完全属于你所创造的世界里。比方说吧,今天,我,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是情郎又是情妇,在一个秋日的下午,于大森林的纷纷黄叶之中策马奔驰,我还是那骏马,那风,我还是出自我的人物口中的词语,甚至是那红日,它让他们几乎闭上了爱已干涸的眼睛。”
如果不读《包法利夫人》,可以谈论福楼拜吗?可以,就读他的书简吧。
禁欲的隐士
福楼拜写信,动不动就写high了,仿佛忘了信本身的功能一样;他要把书信变成一种体裁,而他自己正是这种体裁的巅峰。他似乎预感到,未来人们将不再读纸质的信,从而彻底丧失了一种习惯,一种文化,甚至不能想象写纸信、读纸信的感觉,到那时,会有一些人把他的书信发掘为珍宝。
比福楼拜晚一些的王尔德,在一种世纪终结的压力下,继承了福楼拜的信的作风,以及那种以文字为神圣的使命感。某次,被人问起那天干了什么的时候,王尔德说:
“我整个上午都在为我的一首诗做校对,并拿出了一个逗号。下午我又把它放了回去。”
可以不信这话——王尔德当然很善于夸张;但就像帕斯卡尔用打赌的方式来劝人“不妨信神”一样,我们真不如相信王尔德,因为即使他说了假话,我们也不觉得受了欺骗,反而更能欣赏王尔德的自恋——始终把自己作为最珍贵的艺术作品,为了公众而百般塑造它。而当你读到福楼拜的一封信里说,他花了3天时间做两次修改,又花了5天时间做一次修改,通常平均得花12小时才能写完一页的时候,你就更应该相信他。
如此的迟滞,反复推敲,是为了寻找最准确的词,最准确地表达观点,描绘最逼真的场景,就仿佛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它。福楼拜的自信,在于他认为作家所做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值得付出一生的时间去牺牲,去痛苦。艺术是一种世俗的苦行,是无宗教者的朝圣,披发跣足,斋戒沐浴,一连多少天不沾荤腥,才能体会“残忍的美味”;写东西的人是奴隶,没命地干,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没有书信,我们不会知道19岁的时候,福楼拜曾想过要把自己去势,这是他在给女朋友露易丝的信里说的(露易丝回信问:“什么叫去势?”)。之后两年内,他就不再碰女色了。他没想过两年后该怎么办,在那时的他心目中,阉割就是闭关修炼前的破釜沉舟,相当于你现在为了认真读完一本书而关闭wifi。
克洛伊塞是他到死没有离开过的地方。他被称为“克洛伊赛的隐士”,众多以他为榜样来支持自己的文学平辈和后辈,都忍不住去书写他们心目中这位隐士的模样。毫无疑问,福楼拜不是生而自卑、只能投身写作、避开人群,他是个大个子,金发飘逸,嗓音洪亮,就像2000年前反抗罗马人占领的高卢勇士。当他每年有一个多月住到巴黎的小公寓时,那些名流就都来了:屠格涅夫、龚古尔兄弟、圣伯夫、左拉……精通法语的亨利·詹姆斯也是这些人之一,他用他标志性的辞藻在缅怀文中追忆道:
“他有……一个小小的栖息地,在遥远的、当时几乎是郊区的圣奥诺雷的尽头,在星期天的下午,在一望无尽的楼梯顶端,在一片谈话和烟雾中遇到了大多数巴尔扎克传统之下的小说家……除了谈话,有极大的强度、极端的多样性的谈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
詹姆斯仿佛是在写句子的过程中搜索词汇的,于是主角要在一连串有关时间地点环境氛围的描叙之后才谨慎地出现,句子就如同福楼拜公寓的楼梯那样长而不断,一眼看不到头。晚期的福楼拜很少去巴黎了,就蜗居于克洛伊赛,真正成了隐士,一个独身主义者,像僧侣一样。不过这可能也是被迫,是生理上吃不消的结果。因为1878年,福楼拜给他的一个文坛晚辈、也是有名的梅毒患者居伊·德·莫泊桑(也是福楼拜一位老友的侄子)写去这么一封信,让人读后不由得联想更多。福楼拜劝莫泊桑节欲:
“你抱怨做爱是'单调的'。有一个很简单的补救方法:别做爱……你必须(年轻人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多做些正事,比你做得更多……你生来就是要写诗的:写吧! 其他都是白搭。”
狂喜与苦行
比起一般的书,书信是与纸张联系更加紧密的文字形式。标准意义上的书信,是一些不为发表而写的、具有隐私性的文字,情感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里集中,不加掩饰地流露个性,简单如一个“匆此”“敬上”“盼复”,都仿佛是从写信者心里生生掏出来的一部分;“见信如晤”这四个字绝非说说而已。读福楼拜的书信,岂止是“窥私”,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闯进他的内心。就像开头那封信里的几句话所显示的,他狂喜起来的状态,岂止“漫卷诗书”所能概括——他雌雄同体,他天人合一,他可以融合世上的所有极端的倾向。
在福楼拜和他唯一谈的时间比较长的女朋友——露易丝·科莱的关系里,就是狂喜和苦行一体的。两重性的机制始终在他身上起作用。对露易丝的爱恋,几乎将他赶进修道院甚至沙漠,让他变成一个秘教狂人。她比他大10岁,就像福楼拜14岁时爱上的26岁的艾丽莎·施莱辛格夫人一样(后来他也一直和夫人保持精神恋爱关系),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母般的怀抱。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依恋,甚至还不只是拿对方当纯异性(不管是女友还是母亲)来对待,它还多少表现出他的同性恋癖:他觉得成熟女人身上有男人味。他给露易丝写信说:“我正在向你雄性的头脑表白呢。”“我拿你当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
哪怕他已是150年前的人,读到某些信里的话,正经人都不免为他害臊。福楼拜1846年恋上露易丝,后来,在写给露易丝的信里,他经常绘声绘色地描写自己昔年在巴黎的颠鸾倒凤。比如,他告诉露易丝:“我记得你的手帕,我看到了你的血,我好希望它全是红的呀。”——跟大姨妈无关,多读几封信就会发现,福楼拜喜欢咬女人嘴唇,有一种变态的恋血癖:
“我有一头野兽那样的渴念……一种嗜血的爱,能把肉身咬得粉碎。”
他一次又一次把露易丝弄得哭叫出声:“我咬你的唇:小红点点还在那儿吗?”在两人刚刚建立关系时,福楼拜就说,自己的拥抱如同那些会给母猫放血的公猫一样;当恋情走到尽头,这个猫的形象以一个升华了的形式重现:“我很像老虎,他龟头的顶端长满了虎鬃……用来撕碎女人。”
书信、日记的内容足以改变对一个人的印象。想想那是19世纪,同性恋尚且不为社会观念所忍,而况任何形式的虐恋。很难想象,像詹姆斯·乔伊斯或威廉·巴勒斯这样彻底的现代作家,会没有受过福楼拜的启发和激励。当1856年,《包法利夫人》分六部分在杂志上连载时,其中的通奸和自杀,对拿破仑三世的政权而言实在是过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诉案开始了。福楼拜最终赢得了它,将近80年之后,《尤利西斯》也赢得了一场类似的官司,从而得以不删节地出版。不仅如此,乔伊斯对官司的反应,也跟当年的福楼拜相似:两个人都元气大伤,健康每况愈下。福楼拜在给朋友的信里说:
“这一切让我身心俱疲,连走一步路、捏一支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回去,永远回到我的孤独和沉默中去;什么都不发表了;再也不被人提起。”
这狠话没有兑现,后来他还是继续发表作品。但是他比之前更加回避公众,回避媒体。他在一封信里说出了每个拥有真正的写作才华的人都想说的话:“新闻媒体是一所用来把人变成畜生的学校,因为它让人不必思考。”他拍过照片,但是禁止任何媒体使用他的照片;他也没有接受过采访。这些情况都违反了我们对一个名人的认识——这种对隐私的严密保护足够让他籍籍无名一生。
只显现在作品里
他的狂野暴烈,与他在《包法利夫人》中表现出的沉着冷静,都是真实的,像他自己所说,“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显”。然而,上帝只是“显现”,透过各种异象,例如风雷、大雨、燃烧的荆棘,来发出自己的信号,却从来无人能够看到上帝的模样。这正是福楼拜对自己的定位:只能显现在作品里(从而无所不在),不能被见到。他有过一句话——“在把私人情感变成文学之前,我要被活剥一层皮的”——像是在预估披露他的私人信件的那种可能的情形,又像是在叙述他为了把自己“显现”在作品之中所必须付出的艰苦。
乔治·桑是在《包法利夫人》出版后与福楼拜成为朋友的。桑在日记里说过,福楼拜多次到她家拜访,有一次两人共进午餐,之后跳起了舞:“福楼拜穿上女装,和普劳凯特一起跳卡丘卡舞。这很怪诞,我们都像疯子一样。”在亲密私交的场合里,福楼拜是豁得出去的(不要用“异装癖”这种“新闻媒体”习惯的词汇),然而他断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这般行状会被无数的读者所了解。你若是知道,平时的福楼拜不愿接待任何突然来访的客人,就会觉得他的灵魂也会在你读乔治·桑的日记时局促不安起来。
更不用说他自己的信被人看见了。他实际上是想要毁去一些书信的。1877年,他就跟老朋友马克西姆·杜康约定,烧掉二人1843~1857年间的所有通信,两年后,他又和莫泊桑一起整理了自己平生所收的信件,并把露易丝给他的信销毁。可是他能做到的仅此而已。杜康和莫泊桑都没有依约办事,露易丝也把福楼拜给他的信都留了下来。恐怕只有这样的解释能让他安心:他的信写得太好,就连他收到的信都为之增辉,让人不舍得扔弃。
正如亨利·詹姆斯在《包法利夫人》英文版的序言中所写,福楼拜“生是小说家,长是小说家,活是小说家,死也是小说家,呼吸、感觉、思考、说话、执行生活中的每一项操作,都是小说家的身份”。他的献身精神太过强烈、太过无私,绝对能支持后世的艺术家克服挫折、走出痛苦。他每次提笔写下什么,与其说是在书写,不如说是某种书写艺术在书写他,因为其专注度实在太高了。在中东旅行期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说:
“当一个人做某件事情时,他必须一门心思地做好它。那些整个白天卖羊油、晚上写诗的混蛋日子是为平庸的头脑而设的,他们就像那些同样适合被人骑乘和拉车耕地的马——那是最低等、最差的马,既不能跳过沟,也不能拉犁。”
以这种专注的才华的名义,以《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布瓦尔和白居榭》的名义,福楼拜的那些流淌着虐恋和倒错意味的信中词句,似乎也都无可嗔怪了。这算是艺术家的特权吧?的确是。但只看到这一点也嫌浅薄。我们是再也回不到书信的年代了,不知道写信人,尤其是写信给自己仰慕或爱恋的对象的人,对信寄托了多么深的情感。要么不写,写就要写到让收信人在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它包含了一颗风尘仆仆的心,在读信时,依然能感受到写信人的情感和他留在信纸上的温度。为此,信中的内容往往是过分的,一句平淡的“我爱你”,是不足以抵抗时间和距离的损耗的。
金字塔的塔顶
当然,如果福楼拜的才华并非顶级,他大概率也要承受“以写下许多充满情色内容的书信闻名”的盖棺定论。可他爬到了金字塔的尖端,从而被他所投身的事业给完全地庇护了。这个规律,在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就像美国文学批评界的耆宿乔治·斯坦纳,2007年他78岁,出了一本《未写之书》,其中整整一章,都是用他标志性的华丽语言,描写自己年轻时同9个女人的性爱关系,而且个个不重样。读者买了书,纷纷翻到第三章“爱神的语言”看个究竟。老了老了,名誉地位无可撼动,什么话都可以敞开了说。
可那毕竟是回忆录,可以虚构,可以夸张,我们肯定不希望,一个掘自地下的精美古瓶,是某个颇有心计的古人有意埋在那里,就为了让后人发现的,那样一来,它所要传递的信息的价值就会打上折扣。我们相信书信,正是因为它不骗人,哪怕有意的掩饰也会暴露作者的真相,如同戴着手套作案,也会在物件上留下可以采集的痕迹一般。福楼拜很清楚名誉同金字塔的关系,他在一封信里,以穷形尽相的顽劣说出了大致相同的意思——我们会喜欢这种顽劣,并管它叫“真实”:
“想要圣洁地活着,在干净、新鲜的空气之中活着,就要把你自己放在一座金字塔的塔顶,不管它是哪一座,只要它巍峨高大,底座稳固。啊!那上面并不总是‘好玩’的,你彻底地孤独着;但是,能从这么高的地方往下吐唾沫,会给你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