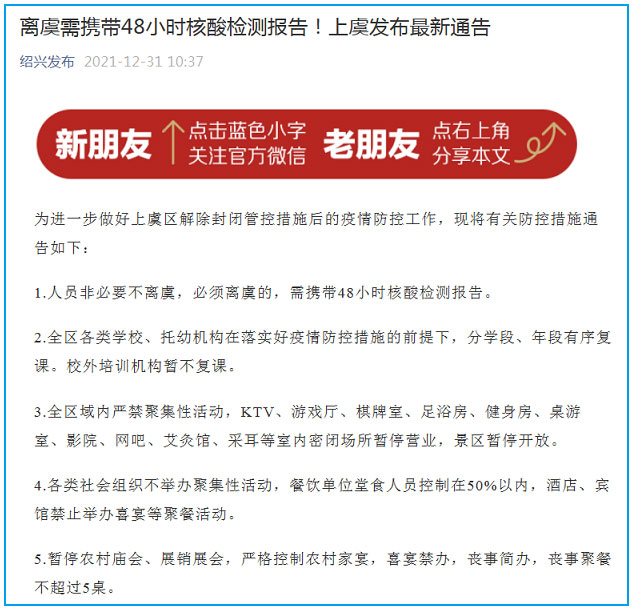大男子主义泛滥且自我反噬的宏观经济学
61岁的戴安·科伊尔(Diane Coyle)是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这位198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女性经济学家,在2014年正式进入大学担任教授前,职业履历丰富多彩。第一份工作是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之后在《经济学人》《独立报》等媒体担任经济编辑,又在BBC电台担任主持人与BBC信托主席,还常年兼任英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顾问。科伊尔虽为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对这门学科,尤其是用来指导政府经济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却有着相当强烈的、与普罗大众颇为相似的怀疑。“当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自身是社会一部分的时候,社会科学真有可能在追求客观吗?”“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经济学表演人格式的自圆其说究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一个个看起来好像小学生提出的问题,科伊尔在她的新书《螺丝钉与魔鬼: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且应该是什么》中(Cogs and Monsters:What Economics is,and What it Should Be)尝试做出回答。
不妨先来拆解科伊尔书名里的隐喻。所谓螺丝钉(Cog),顾名思义,是宏观经济学所预设的参与大型经济活动机器里一个个既不重要又不可或缺的个人。在传统的以供需关系为中心思想的经济学眼光里,个体差异很不重要,螺丝钉没有感情,按部就班,不会集体性做出不符合预设的非理性行为。社会机器的运转离不开螺丝钉,螺丝钉又仿佛并不影响机器的整体运作,只是一个个将被收集整理的数据点。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年代的传播学理论便指出,社会作为“机器”的隐喻常见于我们的日常修辞之中。科伊尔接过莱考夫与约翰逊的理论,并继续指出,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家常把自己比作“工程师”或“水管工”,工作是为社会经济活动设计整体蓝图,之后无非小修小补,改改税率,调调利率而已。经济学家、技术官僚经常陷入一种量化交易一般的机器人视角,习惯用数据、算法、公式抽象地解决不那么干净、不很完美的现实问题,往往令他们自己都目瞪口呆,以至于为了自圆其说,容易矫枉过正。
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为首的技术官僚打出的一系列组合拳,至今备受诟病。人们意识到,整个疯狂的金融体系是模样不为人所知的怪物。在科伊尔眼里,弗兰肯斯坦一般的“魔鬼”行为正存在于经济学家所谓的“无形之手”。事实上,过去十年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已用广泛的案例,反驳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定律,指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并不具备经济学家眼中的完全理性。相反,非理性行为之多、投机行为之缺乏理智、新技术越来越与实体经济和人类生活脱节,都是判定经济学是门“玄学”的重大理由。经济工程师造出的怪胎机器往往不听使唤,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弗兰肯斯坦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并没有纯粹经济活动。所有经济活动都是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延伸。
一个简单的例子,GDP这三个字母,如今好像是衡量我们社会机器运作良好与否的唯一标准。科伊尔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她认为,现代GDP的概念和计算结构来自1930~1940年代,即二战期间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早已不适合当下的经济条件。GDP计算方法只包括“产品”,因此今天大量的新兴经济活动都不在统计范围内。统计局无法统计电子游戏行业有多少无最终产品的交易(如雇人代打、二手市场上的游戏装备交易等),无法统计虚拟币经济的实际体量,甚至依然无法统计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指出,从统计学角度,大量不产生最终产品的互联网服务,如免费搜索、维基百科等,虽然用途极广、造福大众,很可能对GDP反而有负面效益(消灭了黄页电话簿或纸质百科全书等曾经可统计的生产力)。另外,GDP也不会把经济体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其他环保因素作为负面数据统计进去。2009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和让-保罗·费杜西曾经提议用一系列不同指标组成的“仪表盘”(dashboard),来取代GDP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程度的指标。科伊尔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对“生产力”的理解不该局限于物质资料生产力,而应该把社会福祉、人类心理健康、多元化与环境保护等因素考虑进去。
科伊尔的这本《螺丝钉与魔鬼》,其出发点是一个“元悖论”:“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经济学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职业人士一手造就了它所分析的经济体。(经济学家)对经济如何运作的认识及对经济未来如何运作的预期,是我们的理论或‘模型’的中心思想。”简单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患有一定程度的自恋综合征,不但不食人间烟火,还助长自圆其说式的偏见。几个经济学家容易产生的偏见是:过高估计生产力的重要性和人的逐利本能,而忽略很大一部分“人类螺丝钉”并不倾向于追求博弈论意义上的“最佳选择”,如我们常常讨论的“内卷”或“剧院效应”,是所有参与者无论个人还是集体从逐利角度来说的“最差选择”,但依然广受欢迎,好像更接近人的本能;过低估计广告、文化及其他偶然性很强的外在因素对人类选择产生的影响,如美国女性在20世纪初迫于社会压力很少吸烟,但到了20世纪末,在大量广告和女权运动影响下,吸烟人数几乎与男性持平,这不仅与香烟的价格和供需关系完全无关,也不是健康方面的“理性行为”;过度信赖数据,却对数据的来路置若罔闻——收集数据的过程,不像在电脑上跑程序,必须从现实世界里得来,而很多数据工作者全然不具备判断数据是否可靠的现实经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的选举预测算法模型越来越复杂,准确率却越来越低,成了一个全民笑话;对个人特定(ad hoc)的需求缺乏理解,如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欧美国家出现的用工荒,让很多传统宏观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理论上经济刺激政策是为了弥补新冠造成的社会经济活动停滞,一些人却在这段时间看破了红尘,选择彻底躺平,宁可把失业金全部投入股市也不愿再工作,以失业率为一大指标的凯恩斯调控法在这个时段彻底失效,以至于可能出现高失业率、高GDP增长加高通货膨胀“三合一”的奇葩经济现象。
作为相当少见的女性高级经济学家,科伊尔还不经意间提出经济学界大男子主义泛滥、学术文化冒进好斗的特质。经济学家会为了数学模型斗得不可开交,且作为一个集体,求胜欲远超常人。今天,数学能力过强的计量经济学家们,很容易陷入想方设法为自己过于复杂又脱离实际的模型寻找证据,因而彻底颠倒因果关系的谬误。这又与学术界申请经费,各类智库、咨询公司寻找客户的过程直接相关,因为同样由计量经济学家组成的经费评估小组通常(至少申请经费者如此预判)有着一模一样的喜好。这一死循环迅速把经济学这样一门理应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的社会科学推进越来越狭窄的胡同。另外,科伊尔还指出,很多经济学家“真的不够好,或者不够谦虚”。她举出2013年《金融时报》上报道的一个例子:耳机品牌森海塞尔正进行一系列反山寨举措,把自己的损失估计为200万美元一年(接近该公司当年净利润的七分之一)。然而任何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会买假冒森海塞尔耳机的人,或者在地摊上买20美元路易威登假包的人,完全不是这些奢侈品牌的真正用户。他们因为买不到盗版而去买正版的几率非常之小。
然而,尽管科伊尔对当下经济学潮流的批评非常犀利,她这本著作本身却也同样存在“在防空洞里自说自话”的问题。科伊尔的写作无法摆脱一种从各类白皮书和以《经济学人》为首的经济学杂志中推演出来的“流行经济学读本”写法,小标题和隐喻众多,不断重复同样的观点,道德标准很高,但从不提供解决方案。此类写作往往从满地开花的经济学或公共政策论坛演讲稿发展成书,因此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系难以捉摸(比如在本书中,科伊尔不得不在章节之间添加所谓的“中场休息”,来人为制造联系)。科伊尔在书的前半部分集中讨论经济学自我反噬的“心理疾病”,后半部分却很不自然地导入她主要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数码经济。前半部分对经济学的精神分析还没等到被分析对象开口,后半部分便义无反顾走进了新时代,在并不能完全定义什么是“创新经济”的情况下,大举鼓励传统经济学接纳新兴经济的活动方式。这的确是当下缺乏哲学意识的社会科学领域常见的一种奇特现象,连自省都成了范式,最终抵达的结论全部不卑不亢、不痛不痒,仿佛高级螺丝钉不自知的非理性行为。像如今的很多左翼学者一样,科伊尔的论述中反复提到经济学应有社会道德感,承担社会责任,却无法用自己对待“大男子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方式正视自己的道德观中是否存在同样先天(a priori)的偏见,如把生产力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或把“社会福祉”简单化为统计学意义上一份“你快乐吗”的问卷,甚至用一些比较粗鲁、很不准确的比方,如“经济学家通常会因为更多人买丹·布朗的小说而不是阿尔贝·加缪的小说而认为前者的小说更好”,来指责经济学家。
最终,戴安·科伊尔的《螺丝钉与魔鬼》有其潜在的目的性,也就是支持观念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反对计量宏观经济学,支持把当下左翼的道德观念融入经济政策,反对AI量化交易让金融业疯狂生长。然而与她反对的对象一样,科伊尔也可能低估了螺丝钉的多样性,高估了弗兰肯斯坦的能力。而我们的现代经济学,它究竟有什么用处,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螺丝钉与魔鬼: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且应该是什么》(Cogs and Monsters:What Economics is,and What it Should Be)
戴安·科伊尔(Diane Coyle)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