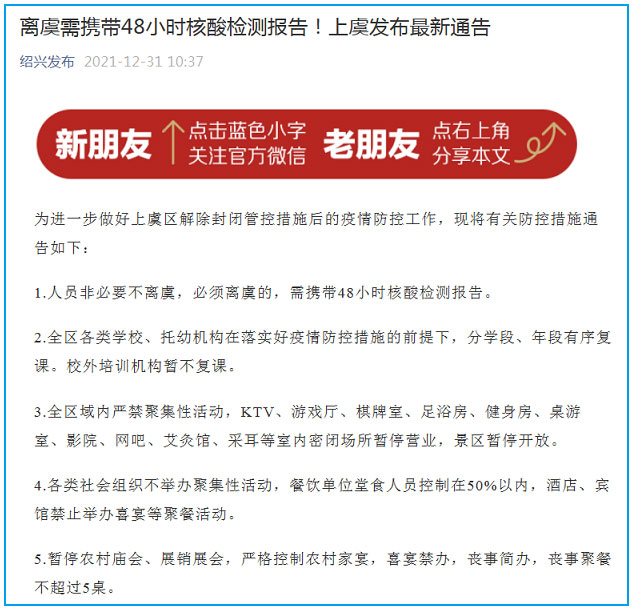朱海斌:经济发展新框架下的新挑战丨首席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展望系列
2021年中国率先退出疫情后的刺激政策。基于中国成功的防疫和经济的领先复苏,这一转变在情理之中。但是,年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退出速度明显超出预期,同期多个领域的行业监管政策接连出台。政府希冀以产业政策的变化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图明显,各个行业发展因此冷热不均,但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复苏的节奏明显放缓。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个三季度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长分别为0.2%、1.2%和0.2%,远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而按两年平均同比增速衡量,GDP增速也从二季度的5.5%下滑到三季度的4.9%。
今年全面而大刀阔斧的行业监管变化,明显与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不同。这一系列政策变化的集中发生,诚然有今年稳增长压力相对较小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展模式的转变。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应地,政策框架也经历了从增速目标制向均衡高质量增长的转型,这意味着实践中的政策目标是多维度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投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实现共同富裕等。
这一政策目标和框架的改变,在今年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行业冷热不均的现象。政府支持的领域,如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与创新相关的高新科技和制造业投资,均表现强劲。反之,政府加强监管的领域,如房地产、高能耗行业、教培和互联网行业,是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源头。
2022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策调整的广度和幅度。政策从高增速到高质量增长、从单目标到多目标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变化。7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屡次强调要做好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这意味着决策层更加着眼于中长期,更加注重政策的连续性。我们的判断是,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明年将不会再现,取而代之的是相对稳健、中性的政策。
与此同时,行业监管政策(如房地产、减碳、互联网监管)的逆周期性减弱,更紧密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以房地产政策为例,我们判断房住不炒的主基调、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三条红线和针对银行房地产贷款的两条红线不会改变,但是监管层会针对当前存在一刀切倾向的严监管政策执行层面进行回调和微调,包括住房按揭贷款发放的正常化、满足房地产企业必要的经营资本融资需求等,以避免房地产行业下行的溢出效应带来经济全面失速的极端尾部风险事件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框架发生结构性转变之后,政策的调整和传导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从今年的情况看,新的政策框架下可能会带来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中,有些是暂时的,有些则需要逐步探索如何解决。
第一个挑战是政策执行。尤其是在监管收紧过程中出现的政策执行过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结构性调整对于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例如 “纠正运动式减碳”,要“先立后破”,要纠正在房地产行业中出现的对开发商全面断贷的现象。这些政策执行中过激的行为部分是因为对于政策变化理解的偏差,相对容易在问题出现后进行纠正。
第二个挑战是政策目标的变化缺乏相应政策工具变化的支持。经济学中的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指出,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且政策工具之间应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当中国从单目标转为多目标后,仍然沿用了以往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当多个政策目标相互冲突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甚至是多难选择。这一点对于地方政府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多目标框架下容易导致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的目标优先次序。各部门会倾向于关注自身的关键绩效指标,而忽略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容易带来政策执行过度、一刀切的现象。
第三个挑战是,在经济目标和框架转型后,政策传导机制和效应往往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整和服务于中长期转型的行业政策出现脱钩之后。如果没有逆周期行业政策的加持,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时效可能会被削弱。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7月降准之后并未带来社融增速的触底回稳,很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政策和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未像以往一样出现逆周期的松动。而在经济结构转型下,央行也更加偏好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降准降息的使用变得更为保守。在这些变化下,可能的风险是传统政策工具的传导效应减弱、传导时间延长,而政策反应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时机,增加未来政策进一步调整的成本。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葛婷婷系摩根大通中国经济研究团队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