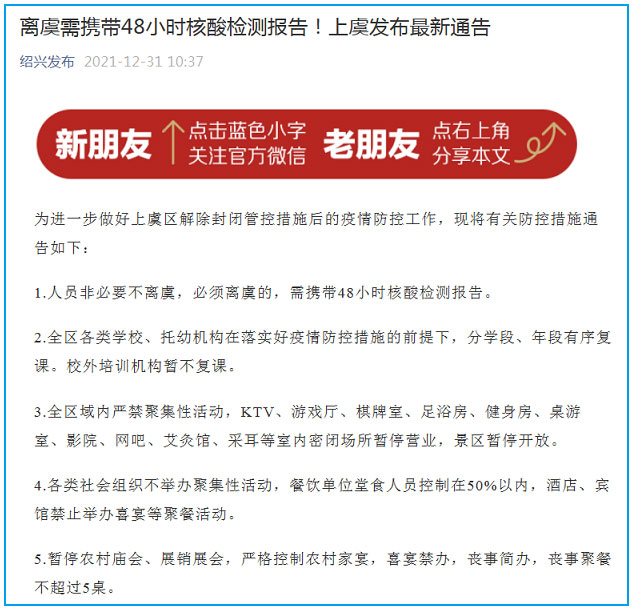张月姣:下笔如千斤,要对当事方负责、对WTO负责、对历史负责
她是WTO里的首任中国籍上诉机构大法官。
入世之后,作为首位中国籍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AB)成员、主席,张月姣在日内瓦工作的八年多时间里,参加了40个上诉案件的审理和交换意见,其中在10个上诉案件审案庭中做首席。
“我在每一个审理的案件裁决书上签名。这是非常严肃的,下笔如千斤,我要对当事方负责、对WTO负责、对历史负责。” 张月姣说。
归国后,张月姣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院长、教授,年近八旬,仍在中国涉外法治领域辛勤耕耘。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对于目前上诉机构的停摆和未来改革方向等问题,张月姣表示,争议解决是公共产品,应快速、高效、正确、低成本解决争议。
她说:“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我建议,在目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级解决争议的机制基础上,增加多元化解决方式和可替代的解决方式(ADR),特别是(可以纳入)磋商和调解(等方式)。”
而对于美方态度,张月姣认为,“美国没有说不回,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也在促进(事态发展),在其他问题上尽量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我觉得大国还是有办法的。”
“在每一个审理案件裁决书上签名”
第一财经:在WTO任AB主席、大法官的八年多时间,对于哪个案件印象最深刻?
张月姣:我很荣幸获得WTO成员方支持,作为首位中国籍上诉机构成员、主席,在上诉机构工作八年多(2007年12月至2016年10月30日),参加了40个上诉案件的审理和交换意见,直接参加了20个案件的上诉审案庭 (Division),其中在10个上诉案件审案庭中做首席。我直接参与审理的上诉案件涉及关贸总协定(GATT)、服务贸易(GATS)、农业协议、技术贸易壁垒(TBT)、商品检验检疫(SPS)、反倾销、反补贴等协议有关的法律争议。
至今每一个案件我都记忆犹新,因为我反复、仔细阅读当事方提交的全部文件,认真听取当事方在开庭中的申诉与答辩以及第三方发表的意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反复研究上诉案件所涉及的涵盖协议,反复推敲思考分析,以便使得所作裁決是公正的,当事方能获得正义,成员间的争议能够获得快速、积极的解决。我在每一个审理的案件裁决书上签名。这是非常严肃的,下笔如千斤,我要对当事方负责、对WTO负责、对历史负责。
举几个例子。澳大利亚涉及新西兰苹果进口争议已经有90多年,墨西哥诉美国金枪鱼进口争议(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未解决的争议),欧盟诉美国连续采取的归零措施争议上诉案件等经过开庭审理,庭审法官合议,上诉机构七名法官在日内瓦内部交换意见,最后由三名庭审法官写裁决报告。
“美国没有说不回,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财经:对于上诉机构的改革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戴琦近期做了阐述,即美方认为上诉机构存在争端解决“替代谈判”和“过度司法”两个问题。怎么评价这种改革思路?
张月姣:对于成员方批评WTO争端解决的问题,我都认真理解并思考改进建议。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四项职能中最成功的,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多边贸易谈判是WTO很重要的职能,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取代谈判功能。WTO是成员驱动的国际组织,成员在提交争议解决之前应该考虑该争议可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 规定双方达成满意的解决协议(MAS)是最好的解决争议的方式。
比如,美国和欧盟的补贴案,他们不拿到WTO(来),是没人叫他们来争端(解决机制)的,都是当事人鼓动、政治驱动的,所以他们说上诉机构或者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替代)谈判,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实际情况。上诉机构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没权力叫他们拿案件来。
第一财经:如美国认为案件不该拿到WTO上诉机构进行审理,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这个机构的运作和权威性呢?
张月姣:美国可以不把案件拿到上诉机构进行审理,中间随时达成协议要退出都是可以的。如果不去上诉机构上诉,上诉机构不处理案件是没关系的,不影响这个机构的权威性,不能人为地非要怎样。当事方要同意,政府更是如此,主权让渡不是无限的。
第一财经:美国还愿意回到WTO改革的谈判桌上吗?
张月姣:美国没有说不回,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也在促进(事态发展),在其他问题上尽量地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我觉得大国还是有办法的。
如何改革上诉机构
第一财经:你认为未来上诉机构应当如何改革?
张月姣:争议解决是公共产品,应快速、高效、正确、低成本解决争议。WTO DSU第3.2条规定“快速、正确地解决争议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prompt, positive solution of disputes is the central element of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我建议,在目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级解决争议的机制基础上,增加多元化解决方式和可替代的解决方式(ADR),特别是(可以纳入)磋商和调解(等方式)。
例如美国、欧盟大飞机补贴案,1992年达成取消补贴双边协议,之后提交WTO专家组,上诉、仲裁、执行时间太长,费用太高。WTO争议解决要防止过度司法化。解决争议的方式由当事方选择,快速、正确解决争议是关键。
争议解决是公共产品,必须正确(correct)、清晰(clarity)、简洁(concise)、协调(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结论公平公正(conclusion of fairness &justice)以及裁决可执行(award can be enforced)。
另外,争端解决机制可限制提交法律文件页数,规定结案时间,严格的行为守守则(Code of conduct),争议解决人员流动性和广泛代表性,不能有利益冲突,独立、公正、专业、敬业。
在“用”中培养WTO人才
第一财经:这些年你呼吁,中国亟需培养国际化的法律人才。何为最优WTO人才?我们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应该如何做?
张月姣:首先,对WTO的规则和国际法都要很熟悉,比如说条约解释和维也纳公约一些典型案例等。而且毕竟是中国法律人,要熟悉中国情况,也要熟悉一些主要国家的(情况)。比如美国的“归零”,要知道归零措施是怎么回事,知识面要相对广阔。不仅法律,政治、经济和技术都要了解,包括电子商务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还有知识产权,都要能够跟上。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复合型人才。对中国来说,外语能力也要具备,因为这涉及法律分析和法律的表达和抗辩,法律的分析和抗辩中也要求逻辑性。这些都是基本的能力,中国学生主要是背书,但是真正能独立地研究分析、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都还不足够。
但这是一个过程。现在国内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在我们已经做过的这20年基础上弥补薄弱环节。我们对一些重点国家,比如美国和欧盟的法律研究还不够,对于WTO一些争议解决的人员背景也不了解,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另外,国内要在“用”中来培养人,所以要多使用中国的律师和专家,专家证人也很重要。
另外,学者的作用也很重要。比如,人家说我们“非市场经济”和“公共机构”等问题,我都呼吁了半天,我们的经济学家动也不动。后来,对外经贸大学的肯尼迪教授(Matthew Kennedy)还写了一篇文章,其他的人(没有行动)。因为作为法官来说,你不能自己提出论点(you cannot make a case),当事方不自己提出,法官是不可能说的,但是你看得出来问题在哪,可提醒之后没有人行动。
我们学术界往往光是评比核心期刊,研究的问题不接地气,不解决我们国家的实际问题。这是一个整体,需要团队精神和综合素质,大家都要关心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比如说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我们要知道这些问题,另外我们如果有对策,要及时地提供给国家,给企业提供最好建议。
法律服务也是如此。所以,我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公共产品,有时候它可能没有利润,做WTO案子也是,因为这方面的案子很少,可能培养了很长时间但就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你就要不断跟踪、不断研究,要看其他的案子,要不断地评论类似话题。
第一财经:未来该如何在世界贸易规则中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张月姣:对于国际关系的法律问题、大型案件,要深入研究,提出中国主张。国内研究院所和职能部门对我国与外国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提早研究对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和平发展、“一带一路”等政策研究并发声,参与国际治理和规则谈判,献计献策。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贡献中国智慧。
我觉得现在我们日内瓦代表团使团做得还是很好的。在这些谈判中,我们能和其他主要贸易方,比如能够与美国和欧盟交流、交换意见。最近67个成员方达成了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在WTO谈判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有疫情严重的情况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