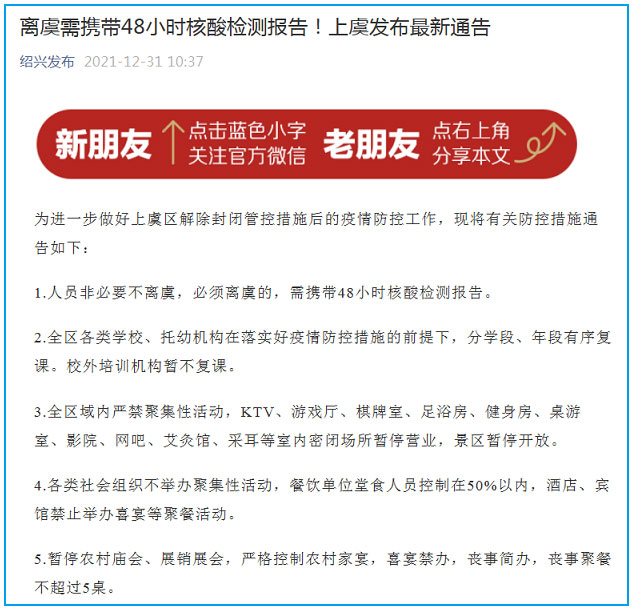WTO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入世20年论
2001年12月11日,经过近6年的艰苦谈判,我国终于成功叩开世界贸易组织(WTO)之门。全世界都对中国的加入充满好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会给这个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国更是激动而紧张:因为世界市场对我国敞开了大门,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外部需求;与此同时,外来的商品一定会冲击我国先有的产业体系,造成一部分产业在竞争中萎缩。因此,不光媒体和普通民众有“狼来了”的惴惴不安,国内外的学者也普遍认为WTO一定会对我国的产业造成结构性的冲击: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获益扩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受损收缩。
然而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扩大效应远远大于行业竞争效应。WTO红利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测。仅仅用了10年,我国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其中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从2003到2007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一直都保持强劲的两位数增长。我国的人均GDP也迅速从2000年的不到1000美元,跃升到了2011年近6000美元,2020年我国更是跨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GDP达到了10267美元,在加入WTO之后的20年间实现了10倍的增长!
加入WTO之前普遍担心的产业大调整并没有发生,我国不但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享受了WTO红利,在电器甚至电子行业也逐渐打开局面。在当下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有部分美国右翼政客甚至叫嚷,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战略失误就是“允许”中国加入WTO。
今年是我国加入WTO的20周年。虽然WTO的红利期已逐渐消失,但是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对我国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首先,WTO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功,再次证明了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三次快速发展期。第一次是我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1980年的深圳特区建立为标志。通过深圳的“试水”,引领全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第二次是浦东的开发开放,标志是1990年外高桥保税区(我国第一家综合保税区)的建立,我国的对外开放从简单的加工制造升级到了基于加工制造的研发和金融等产业链的综合开放。
第三次就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按照WTO的要求,我们不但显著地降低了关税,关税总水平从2000年的15.3%下降到了2010年的不到10%(目前进一步下降到了7.4%);而且还打开了大部分的制造业市场,使得制造业各产业出现了国企、民企、外企(含合资企业)三足鼎立,逐鹿市场的竞争局面。在开放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市场经济得以再次快速发展,奠定了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其次,“开放”不是目的,而是倒逼国内改革的手段。
因为我国是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所以实际上我国本来是有机会以创始成员身份在1995年就加入WTO的。然而,由于担心开放会对国内产业造成巨大冲击,我国迟疑不决。仅仅在WTO形成一年以后,中国迫于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的压力,又重新在1996年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入世谈判,在做出了远比1995年更多的承诺之后才在2001年底最终加入。
然而,实际结果是WTO非但没有冲毁我国的制造业,反而还使我国制造业占领了大量的国际市场。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应对WTO的挑战,开始认真地在制造业中实行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大幅减少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通过优胜劣汰打造了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才为我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6年多的WTO谈判实际上不但为我国赢得提前适应WTO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为国内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
再次,WTO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开放”概念的含义在不断升级。
如果说我国1980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迎接全球化的开端的话,那么2001年加入WTO则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肇始,而2010年以后,我国推动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即RCEP,2020年11月正式形成,2022年1月实施)和“一带一路”,则可以认为是我国引领全球化、树立中国在国际经贸改革中的话语权的探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我国已经从简单的“大进大出”式加工贸易升级到了从研发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随之而来的是对我国开放要求的提升和我国自身对于维护全球化的责任体现,我国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开放义务。
最后,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需要快速而高效地迎接后WTO时代的到来。
WTO对我国的挑战主要是在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在这方面的开放中我国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然而,自2008年以来,国际经贸合作进一步要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形成了所谓的“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要求。概而言之,所谓“高水平”,就是指不光要在货物贸易方面实现全面的零关税,还要在数字通信、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贸易方面实现自由开放;不光要减少在关境上的贸易壁垒,也要大幅度降低在关境内(即国内市场)的壁垒,如政府的市场竞争管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标准和规则的统一等。也就是说,WTO的经贸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关境上,而“高水平”的经贸合作要求则大大延伸到了关境内(即一国的国内市场)。
国际上的第一个“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就是2008年美国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2017年美国退出以后改称CPTPP)。比如TPP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投资准入,以排除法的方式规定外国投资者的准入领域,使得本国很难再以复杂的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随意控制市场准入和竞争。
“法不限制即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个负面清单最直观的解释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负面清单的法律性质和对外企的开放程度,而且意味着在市场监管中行政权向法权的全面让渡、对特定行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特殊政策的减除以及对行业准入和营销的歧视性政策的移除。原因很简单,负面清单之下只能有一种国民待遇,国企、私企和外企应该被一视同仁。
事实上,我国自2013年开展的自贸区开放创新试验就是为了适应国际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要求,我国最早的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向高水平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要求看齐,这样的战略举措无异于在积极准备“二次入世”,虽然开放挑战严峻,但是改革意义重大。
我国在过去的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经受了多次严峻的考验,每一次考验都伴随着重大的改革思路的激荡。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主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90年代初是“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型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加入WTO之后是从“以劳动力换市场到以市场换市场”的突破。每次重大改革思路的落实都有赖于壮士断腕般的改革魄力和勇往直前的执行力,这一点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尤为明显。
无论是前端的关税下调、外贸权“下放”,还是后端的国有企业改革,制造业市场放开,今天看似波澜不惊的改革在当年都是在诸多争议和阻力之下坚决推动完成的,最终通过WTO带来的全球市场,造就了我国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当今世界,制造业的开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合作的要求了,连WTO本身的改革都已箭在弦上,因此我国也正面临着二次入世的压力。
如何将我们相对封闭的服务业与世界连接,如何将我国的市场通过规则和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继续开放,是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党和国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乃至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伟大决心已下。我国推动的RCEP不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区,而且是我国历史上领导形成的第一个(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
时代在改变,我国已从一个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变成了一个一边适应新规则、一边创造新规则的全球化主要参与者,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还需要我们继续用智慧和勇气去推动和实现。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