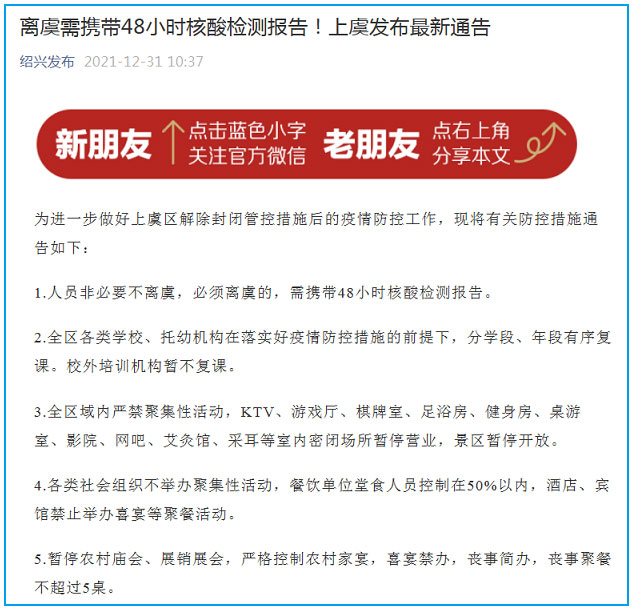内卷化的勤政:晚清靠这些显然无法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大多认定,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当然,也不乏有人将清朝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上溯至更早的嘉庆时期,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真正感受到危机和变局,其实是从咸丰朝(1851~1861)开始的。这一时期,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列强进逼,连首都北京也被英法联军攻破,清朝内政外交均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自此以后,权力下放,地方督抚主导了变法自强运动,但如果是这样,那当时朝廷在做什么?
毫无疑问,就像历史中的所有人一样,哪怕清廷上下在最初遭受冲击时张皇失措,但总会以自己的方式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反应,因为很显然的一点是:就算他们仅仅只是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在新形势的倒逼下,也不得不做点什么。
和历代王朝一样,清朝原本的统治所依靠的,是一套复杂有序的文书行政系统,中央的政令正是由此才得以传递到帝国的每个末梢,并得以有效执行。而中枢的政治决策,则由君主和各部院、封疆大吏经由朝会商讨决定。
不难看出,按照这样的设想,国家的有效治理最终应当取决于君主的“勤政”与臣下的勤勉配合。所谓“辨色视朝”,本意就是指每天朝廷上下天蒙蒙亮就开始治国理政,而清人也确实比历代都更严格地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年间还上奏说:“辨色视朝,为我国家一定不易之家法。”不管后世学者对清朝统治有何看法,有一点不可否认:清朝诸帝确实比历代君王都更为勤政。
按照清代的制度设计,这原本可说是最完美的体制。正如李文杰在《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一书中指出的,清制为大臣设置了权力的“天花板”,尤其是雍正设立的军机处,更是清人“深感优越和自豪的制度”,实施的100多年中,“能彻底阻隔权臣奸相这个对天下安定具有毁灭性的元素的出现”。虽然晚清遭遇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打乱了原有的朝会议事和文书处理流程,改变了原有的决策机制,但人们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只要君臣一心、勤勉谨慎,那么理论上说国家就能实现长治久安。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一期望落空了,这并不是因为晚清君臣不勤勉。尤其是1889年接受归政后的光绪帝,给自己定下苛刻的时间表,每天处理政务的起始时间比前代清帝大为提前。光绪年间御殿听政,臣子们0:30起床,1:30下园,3:45到园,5:15开始朝会,皇帝也同样遵行,以至于其生父醇亲王奕譞都上奏建议“视朝不宜过早”。然而他们忙忙碌碌,听政本身却逐渐沦为一种象征性程序,“从原有的重要政务商讨,逐渐演变成例行公务,它对国家政务的影响减弱”,到头来,“这种重在形式的朝会,牺牲君臣的健康,代价实在不小,就政务运作的实际效果而言,作用却不大”,变成了一种徒耗精力的形式主义和君臣的负担,甚至有还不如不搞。
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时局下,国家治理所遭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可能催生海量的问题,仅凭皇帝个人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根本不足以应对,哪怕光绪帝锐意求治、将辨色视朝的祖制做到极致,也仍然一样。可以说,这种“内卷化的勤政”只是让人们疲于奔命,甚至损害健康,但朝政却仍然糜烂。这充分表明,当时面临的是全新的全面危机,传统模式即便发挥到极致,仍然回天无力,只能改变机制、另寻出路。
当然,对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来说,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特殊情形:“垂帘听政”之下,朝廷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被“虚君化”的皇帝再怎么勤政,对现实政务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所有人不过是“认认真真走过场”,煞有介事地“表演”而已。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权力中枢并没有瘫痪,但它却已经不在皇帝那里,这就愈加使得其勤勉远离其预期所要达到的效果了。
朝廷也不是没看到形势发生了变化,1861年成立的总理衙门就是明显一例。中国很多现代化的官僚机构都是从这一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然而深入剖析其运作机制就会发现,它仍然延续了传统的做法,必须全体大臣合奏才能发出。这就意味着,任何试图打破成规的创见都不太可能获得十余位总理衙门大臣的一致赞成,只有最稳妥、保守的建议才最保险。这样的制度设计,本意旨在将责任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牵制任何权臣威胁皇权,然而这样一来,在日新月异的剧烈变动面前也就势必处处被动,很难真正应对时局。
由此也能看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巨大的惰性:尽管外部挑战已经极为严峻,身在其中的人也都感受到了,但即便看似现代的理念引入、创设新的机构,但在这背后,人们其实仍然根据传统的观念来理解吸收。对当时的衮衮诸公来说,即便要考察西方富强的奥秘、引入议会制度,但重心仍是改善“下情上达”,“师夷长技”乃是为了“中体西用”,补足中国原有机制之不足,而不是另起炉灶。
因此,人们似乎尝试了各种办法,却还是在原地打转。西式的“民主”,在清廷决策中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精英民主”,看上去集体参与、多人发言,但人人怕担责任,集体决策往往就朝着最平庸安全的方向靠拢。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谴责说:“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个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李文杰也相信,这种“形式上的精英民主,不但未能发挥民主决策的作用,反而成为合理决策的障碍”。
然而确切地说,“民主”仅仅只是“集体商量”吗?这恐怕本身就是对西方思想的重大误解。在表面的相似之下,清廷那种合议,与当时西方列强的议会民主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合议达成的共识,也和西方那种各利益集团通过激烈的博弈达成的共识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李文杰在后记中认为历史学不必赶“跨学科”的时髦,“越是将本学科做到极致,便越能贡献给其他学科”,但他的论述却正表明,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引入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是很有必要的。
这或许也意味着,即便如今凭借后见之明,历史学者仍然不易为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找到打破困局的办法。那部庞大的机器,即便仍然一如既往地维持着运转,但却越来越难以有效影响现实社会。与此同时,它还有让人产生一种“我已经很努力尽责了”的错觉,其实却是在逃避真正的改变。不管怎样,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帝制时代的中国如何维持运作,也彰显出当时的危机之深重:仅靠对原有机制的修补无法应对火烧眉毛的难题,老办法即便发挥到极致也仍然无法解决新问题。
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晚清史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晚清地方督抚和下层精英的兴起,恐怕并不仅仅是由于湘军、淮军等地方实权派在太平天国战乱后的坐大,也是因为在接踵而来的危机面前,身处前沿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随机应变,而当他们一次次比朝廷中枢更能有效应对局面时,就势必引发决策机制和权力结构的变动。吊诡而令人深思的是,朝廷通过“勤政”没能挽救危亡,而对地方的放权、激发民间社会的活力,最终反倒在无形中为清王朝延命了。
《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
李文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