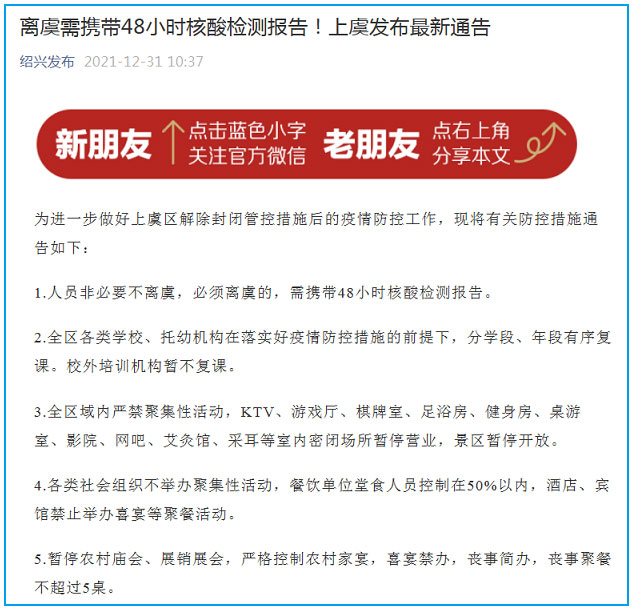陆铭:以空间结构政策化解债务、房价和通胀的矛盾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着降债务、控房价和抑通胀三个宏观目标,但在具体制定政策时,这三个目标有时候会出现相互冲突。理解并解决这种冲突,需要从空间的角度把握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和问题症结,从而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从资源空间配置角度理解高杠杆、高房价
近年来,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但是不管是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还是家庭杠杆,都需要分地区来看。
从地方政府来看,债务-GDP比率(即负债率)比较高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原因主要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平衡区域发展,这些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不够好,事后没有足够的回报来偿还债务,反而给未来发展带来较大负担。相对应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债务总量虽然也不小,但是经济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负债率相对比较健康。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在区域平衡政策的影响下,在建设用地指标和劳动力流入等方面相对受到了抑制。近年来,在一些经济活力旺盛的特大和超大城市,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不可否认仍存在限制土地供应和人口流入的政策,这使得相对于保增长的客观需要而言,改革仍然存在较大空间。
从家庭杠杆来看,杠杆率比较高的是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由于这些地区房价高,所以虽然家庭负债率高,但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却并不高。如果房价不出现剧烈的波动,那么伴随着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这些地区的家庭杠杆率风险是总体可控的。相反,在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地区,家庭的负债率虽然相对来说不高,但是反而有可能因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而出现后续需求不足,房价下跌空间反而较大,使得家庭杠杆不可持续。因此,以发展的眼光和空间的视角看,防范家庭债务问题需要谨慎关注人口流出地由于房价下行带来的压力。
影响当前居民杠杆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房产价值,而面对控房价的问题,如果仅仅看全国的房价-收入比,非常容易得到一个误导性的结论,那就是持续的房价收入比提高可能隐含着巨大的泡沫。然而需要注意到,中国城市房价的分化是随着2003年以来土地资源空间配置调整产生的。研究显示,如果将中国城市分为人口持续流入但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组别,以及人口相对稳定甚至流出,而土地供应相对放松的组别,那么中国高房价收入比的城市主要是前者,而后者的房价收入比却是水平低且呈下降趋势的。从空间上看,人口流入且土地供给相对收紧的城市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人口流出且土地供给相对宽松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
如果不做上述区分,就会只看到全国层面的平均房价收入比上升,而这其实主要是由少数土地供不应求地区的房价收入比上升所驱动的。于是,如果忽略了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的背景,直接把个别地区的住房短缺问题理解为全国层面的泡沫问题,那么政策上便会采取抑制购房需求的政策。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按照家庭拥有住房的数量和面积来对需求进行控制,有助于缓解社会的财富不均等。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严控需求的政策已经把炒房空间压得很小,一些真实购房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资格购房的人群因为贷款收得太紧而弃贷弃购,这便与制定政策的初衷相背离。另外一方面,在多年以来的控杠杆、控价格等政策作用之下,房地产开发商财务状况恶化,进一步拿地的能力和意愿下降,而且在建房屋质量又会受到成本限制的影响,业主投诉事件频发,这既不利于在人口流入地持续增加住房供应满足人民需要,又不利于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债务的空间属性与通胀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在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下,忽略债务的空间属性将使得通胀问题更为棘手。由于当前的地方政府高负债率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潜力较小的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自我偿还债务的能力较低,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一边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逐步化解欠发达地区的债务存量,一边要渐进地打破刚性兑付来控制债务增量。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来源,主要是较发达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当整体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时候,如果不加快释放较发达地区的增长空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只能被迫选择采取总量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债务压力,而这难以解决结构性的增长差异问题,更会带来严重的通胀问题。
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受到疫情的冲击,政府宏观政策偏松,信贷发放量增长较快。在信贷大量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实体经济增长空间得以释放,那么,以上矛盾能够得到缓解,但空间的差异化并没有在政策中得以体现,而一些散发疫情和部分地方政府采取的一刀切政策,更间歇性地打断了原本正在恢复的经济增长趋势。民间的消费和投资积极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更大。
在货币宽松和增长趋弱的组合下,一些信贷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大城市总体上存在住房供求失衡的状态下,资金的进入就导致了2020年一些大城市房价的上涨。而这一轮房价上涨,引起了更为严格的购房需求管理措施,又反过来加剧了前面所讲到的误伤刚需的结果。一旦从需求侧打压房价,流动性就又进入到商品和服务领域,于是,由物价上涨所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
关于空间差异化结构政策的三点建议
由于当前几个宏观目标已经远远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用结构化政策来化解债务、房价、通胀之间的矛盾,而其中的重点是考虑空间差异的结构化政策。
第一,最为重要的是保增长。
一方面要释放优势区域,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和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引领作用。对于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制约大城市增长的因素要继续深化改革,在资源的空间配置中尊重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要调整其他对于经济增长不利的政策。比如在未来一段时间,谨慎出台抑制需求的政策,对于运动式减碳和教育减负等政策执行中对于实体经济的“误伤”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
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家,要形成政策稳定的发展空间和未来预期。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要贯彻中央所提出的“先立后破”的原则,以法治为准绳,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2022年,随着欧、美、日等经济体逐步恢复经济增长,出口的带动作用可能会相对减弱,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政策上要为保增长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在化解债务风险方面,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人口流动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
对于人口流出地,以保持能够偿付利息为原则,严控债务增长,而在化解债务存量的同时,财政转移支付重点关注民生领域,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人口流入地区适度放松对于政府债务的控制。建议试点发行有利于城市化和促进人口流动的“市民化专项债”,专门用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优势地区对于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
第三,基于对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互替联系,伴随着即将实施的房产税改革,建议对基于有效需求的购房者适度放松限制。
如果房产税改革是在少数试点城市推开,那么有必要在试点城市对于购房的资格、信贷等适度放松。对非本地户籍人口获取购房资格的社保缴纳年限适度调低。通过这些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房地产税对于房地产市场形成过大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释放购房者的真实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缓解经济增长降速的压力。
此外,在人口持续流入地区要加快改革,继续多渠道增加住房供应:使建设用地指标增长与人口总量增长相适应;加快人口流入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进程;加快闲置工业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的转换;对特大和超大城市住房用地的容积率放松管制;加快发展租赁房市场,特别是长租房市场。通过以上几方面综合施策,从供给侧缓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同时,也可以通过释放房地产市场上的真实住房需求,吸纳流动性,缓解物价与服务价格的上升。
(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李鹏飞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铭心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