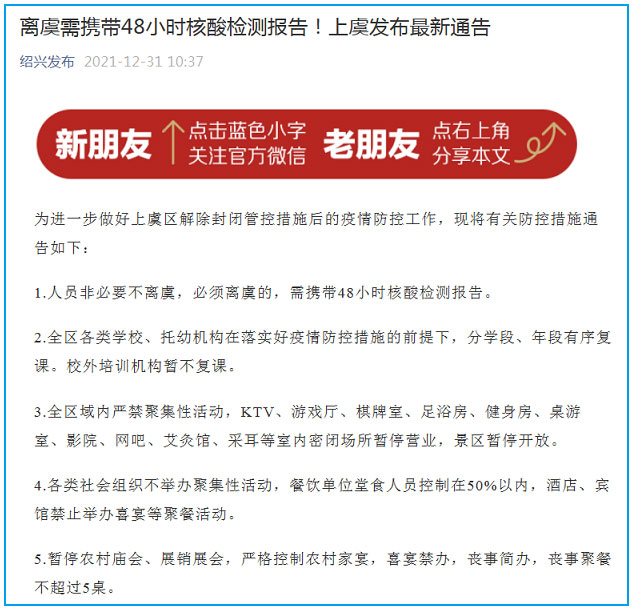长江商学院教授刘劲:如何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建立是通过一系列的契约关系: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公司与公司的上下游之间,公司与政府之间,公司与社会之间,等等。我们一般说公司是股东拥有的,是因为股东掌握最终对公司资源调动的控制权。但如此复杂的契约关系说明企业绝对不是简单地属于股东。追求股东利益是股东的核心诉求,但公司在同时必须满足其他的契约条件。股东们为了分红,必须先付掉员工的工资,供应商的应付款,银行贷款的利息和本金,国家的税收,等等,有了剩余才能轮到自己。
由于股东在现金流上的绝对滞后,一般来说,在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已经满足了其他契约关系中的主要责任。所以,在像美国这样的绝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提倡的是企业都应该心无旁骛,应该一心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美国人不是说企业可以唯利是图,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事情,而是假设这些事情都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但德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为股东不能代表企业的所有参与者,因此员工代表、给公司授信的银行,在公司管理中也有很强的话语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更加复杂,大股东不仅要追求财务回报,还要完成诸如社会就业、行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刺激等多种政府意志,因此在市场中的行为与私营企业有很大的不同。
在企业错综复杂的契约网络里,有些东西是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表达的,比如公司章程、高管的聘用、激励机制、员工的雇佣合同,公司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合同,等等;另外的东西是不属于法律的管辖之下,而属于隐性的契约,比如公司实控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股东认为高管和员工是资产还是费用,公司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态度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公司在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冲突时应该如何做出抉择,等等。总之,即使在法律最健全的社会,企业所牵扯到的契约也不可能完全被法律正式覆盖,相当大量的责权关系是属于隐性的、不完全的合约。出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诉诸公堂,而是通过文化和道德的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褒贬。
中国和西方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中国政府对社会有超强的影响力。政治部门、行政部门和法律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有一致性。因此,在中国,文化、道德、行政规则、法律所管辖的范围也就没有西方分得那么清楚。在很多时候,违反主流文化或道德标准所受到的惩罚,比违法的惩罚还要来得迅猛、严厉。这是中国企业必须弄清楚的一点,中国的经商环境和西方的经商环境有本质的不同。
那么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就是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律和行政规则之外的文化和道德约束。相对于遵纪守法来讲,社会责任的考量更加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和道德是隐性的,经常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下来,或者是散落在很多不同的文字来源中,因此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原因是文化和道德是动态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因此企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经常会追不上文化和道德的发展。四十年前的大学里,晚上老师还要拿着手电到学校的小树林里抓“伤风败俗”的谈恋爱的情侣,“宅男宅女”才是模范行为;二十年前企业的工业污染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只要能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就行 ;十年前大声疾呼碳排放的问题的人还会被认为是激进的愤青。
文化、道德的变化,与法律、行政规则的变化比较,速度更快,更具有前瞻性,体现在当下的文化和道德里的东西,到了将来就可能变成法律和行政规则。反过来说,法律和行政规则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如果不注意文化和道德的发展,而只注意遵纪守法,就自然应该在某些领域为没有承担“社会责任”而受到社会的惩罚与制约。
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大的趋势正在推动文化和道德的发展。最明显的是环境保护问题,其中,全球气候变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子问题。这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集体遭遇到的最为危险、最难解决的重大课题。到目前为止,在法律和行政规则方面,全球还没有对解决这个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各国各行业还在为谁来负担成本讨价还价,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企业,如果走在降碳和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最前沿,自然会受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拥戴,就是尽到“社会责任”的典范。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除了科技创新和优秀的经营基本面,不得不承认,马斯克和特斯拉之所以受到全球的狂热追捧,和其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很强的关联。
除了对环境的关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对极端市场状态下导致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也令人们重新反思原有制度安排的不足之处。在中国,“共同富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税收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没有对贫富分化做出明确的反应前,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就会从善待自己的员工做起,提高劳动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适当减小收入差距,最后在管理层、投资人个人层面再用慈善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不这么做当然不会触及法律,但一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然后会损害品牌、减少收入、降低利润率。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越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反倒收入增加越快,利润率越高,股价增长越快。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巨头在全球的崛起是商业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事件之一。像亚马逊、谷歌、脸书、阿里、腾讯这样的企业,一旦占据了互联网的流量入口,规模效应成级数增长,几乎可以到任何一个行业(尤其TO C的行业)兴风作浪,颠覆原有格局。但同时,其竞争逻辑也由初期的科技创新逐渐演化到后期的垄断力支撑下的零和博弈,从而使这些公司的利益从和社会利益高度吻合逐渐演变成相当对立。有“社会责任感”的做法是要清楚地感知到这种变化,继而调节公司的竞争政策,让权、让利于竞争生态和广大用户。可惜的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大多保持了企业初创期的狼性文化,在公司已经有巨大支配力时,仍然把力用到百分之百,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所以最后迎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制裁。即使像“不作恶”“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样的初衷也无法阻挡社会对这些公司继续高速发展的担忧和不满。
最后,由于“社会责任”来自于社会,不同的社会对企业的要求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中国,华为实际从体量和影响力上都超过了阿里和腾讯这样的巨头,但并没有受到反垄断制裁,甚至很少听到社会的非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为的成功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效应或网络效应。科技升级是中国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尤其在中美科技脱钩的大背景下。所以,华为的股东利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高度吻合,华为越大,中国就越强。华为的公司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社会利益。如果阿里和腾讯也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科技创新上,帮助解决中国在科技领域里的诸多卡脖子问题,中国社会自然不仅不会限制它们的自由发展,反而更可能用舆论和钱袋子实打实地支持它们。
企业管理是一件复杂的、永远在变化中的事情。企业小的时候,创业者只需要做一个好的管理学家,把企业经营好,让企业活下来。企业大了以后,企业家就不得不变成经济学家、政治家,从更深层次重新审视企业的所有侧面,从各个层面让企业发展的利益与社会利益高度统一,这样才能获得基业长青的基本条件。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